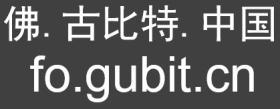侧边栏
从艺术史的角度溯源藏传佛造像
藏传佛教属于喜马拉雅文化的一部分,与南亚次大陆、中亚和西亚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另外,藏传佛教是南亚的佛教文化与雪域高原的游牧文化结合的产物,它有着异域的血统,但是始终扎根于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土壤。其流传范围以喜马拉雅文化区为中心,延伸至蒙古高原、横断山脉、天山南北等广大地区。
因此,如果想真正理解和深入解读藏传佛教艺术,必须回归青藏高原丝路、南亚次大陆等多元文化的语境,在喜马拉雅文化的大舞台上,从中亚、西亚和南亚文化的多重影响来重新审视和研究它的起源与流变。
喜马拉雅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南端,东西绵延2450公里,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的天然边界,给山脉两侧的文化交流带来巨大的障碍。但喜马拉雅山脉纵横的沟壑与河谷也像一个个管道,将青藏高原与丝绸之路对接起来。其中主要有两条路线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产生过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一条是西北印度,来自西北印度的艺术中心犍陀罗、斯瓦特、克什米尔的艺术影响进入藏西的拉达克、阿里等地区,创造了独特的藏西风格;一条是东北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裂隙,将中国西藏中部与东北印度和尼泊尔两个重要的艺术中心相连,是藏中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本次“佛陀之光”(The Light of Buddha)展览共展出112件造像作品,时代跨度从4世纪到15世纪,涵盖了藏传佛教艺术上述两个主要来源。
当然,112件展品对于广大观众了解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起源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梳理1至15世纪印度、喜马拉雅到青藏高原艺术发展的脉络,让读者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
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重要时期:贵霜时期(1世纪晚期—3世纪)、笈多时期(4—6世纪)、区域风格时期(7—14世纪)。
犍陀罗与秣菟罗:
奠定印度艺术基础的两个中心
众所周知,佛陀形象的雕塑出现在1世纪的贵霜王朝(Kuāa Empire)。它的两个重要艺术中心犍陀罗(Gandhāra)与秣菟罗(Mathurā)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对印度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犍陀罗
犍陀罗大致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喀布尔河与印度河交汇的白沙瓦(Peshāwar)谷地,是贵霜王朝的核心地区,首府为呾叉始罗(塔克西拉,Taxila)。犍陀罗扼丝路之咽喉,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本身又是佛教信仰中心之一,再遭到西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冲击,形成了独特的国际化的文化与艺术风格。(注1)
广义上的犍陀罗风格涵盖的区域还包括北部的斯瓦特(Swāt)河谷、喀布尔以东的迦毕试(Kapia)以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Bactria),即今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所以有人主张应当用“大夏—犍陀罗(Bactro-Gandhāra)风格”来替代“犍陀罗风格”。(注2)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在其两本研究铜造像的巨著里分别将这一地区的范围清晰地列举为“犍陀罗、斯瓦特、兴都库什”以及“大犍陀罗、斯瓦特、兴都库什、帕米尔”(注3)。因此,犍陀罗艺术实际上存在众多的地区风格,而不是指一种小范围的、完全统一的风格。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末兴起后,其艺术中一直没有佛陀形象的表现,遇到应该出现佛陀形象的地方均以脚印、宝座、法轮、菩提树、佛塔等作为象征。1世纪后,大乘佛教的流行为佛陀造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犍陀罗地区,现存最早的佛陀像约出现于1世纪中叶,2世纪末至3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造像的成熟期,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塑艺术的风格,高鼻深眼,头发呈波浪形并有肉髻,身披厚重外衣,立姿像一膝略屈,颇有动感(图1)。材质以灰色片岩、石膏居多,陶质(terra cotta)次之,象牙和金属造像最少。
秣菟罗(马图拉)
另一个重要核心秣菟罗是贵霜王朝的冬宫,位于北方邦(Uttar Pradesh),亚穆纳河(Yamunā)右岸,德里(Delhi)东南,据水陆交通之便,自古以来就是印度北路和南路两条交通的连接点,也是印度与丝绸之路沟通的枢纽。自巽伽王朝(unga Dynasty,公元前187—前78)以来,这里就成为印度重要的艺术和商贸中心,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三教兴盛之地(注4),与犍陀罗齐名,也是最早创造出佛陀形象的地区之一。
如果说犍陀罗是国际化的艺术风格,充满异域风情,秣菟罗的艺术则可称为印度本土风格。佛陀像高大魁伟,发髻如海螺状卷曲,盘在头顶,光滑无纹,表情严肃,身体挺直,上身着轻薄贴身的袈裟,衣纹密集,着力表现人体轮廓。(图2)
笈多艺术:
印度黄金时代的艺术典范
贵霜时期为后来印度艺术的分野奠定了基础,但也推动了印度艺术改革另一个高峰的到来,最终奠定了两个艺术风格的面貌。这次变革的中心转移到印度北部广大地区,就是笈多艺术。
笈多王朝(Gupta Dynastry,4—6世纪)是印度历史上短暂的相对统一的时期,也是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大繁荣的时期,被史学界称为“黄金时代”(Golden Age)。笈多文化体现出印度本土艺术精神,奠定了印度艺术的美学基础。笈多王朝崩溃后,其余波一直延续到7世纪,被称为“后笈多艺术”(Post-Gupta Art)。笈多艺术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就是恒河流域西段的秣菟罗和偏东段的萨尔纳特(鹿野苑,Sārnāth)。
笈多王朝造像较之贵霜王朝造像,主要的不同点如下:佛像发式以印度式细密螺发为主,成为笈多艺术的标志性发式;服饰放弃犍陀罗式的宽厚袈裟和自然写实的衣褶,秣菟罗造像以规律的细密条棱衣褶为特征,萨尔纳特则完全不表现衣褶,袒裸一肩的贵霜样式并没有流行,以着通肩式袈裟为主;袈裟紧贴身体,充分展现富有弹性的肌肉和圆润的双腿,配合光滑的额部和面庞,低垂的眼睑以及修长的身材,构成完美而又标准化的人体,神情沉静安详;以不同花鬘组成多重纹样和贝壳边纹装饰的圆形头光。
5世纪晚期至6世纪菩萨造像日渐增多,有复杂的发髻变化和丰富的装饰品,身体略前倾,垂目下视,身材修长,气质安详,披圣索或胳腋,着薄短裙,紧贴双腿,胯部系粗大的腰带,明显带有印度教艺术的影响。(图3)
笈多时期印度造像以石材居多,比如在秣菟罗以红色砂岩为主,萨尔纳特以浅黄色砂岩为主。这一时期铜造像数量明显增加,陶制造像从西北印度到孟加拉地区均普遍存在,主要用于寺庙与佛塔装饰。
在西北印度地区,3世纪后,犍陀罗艺术逐渐向贵霜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发展,5世纪时,贵霜王朝瓦解,但犍陀罗艺术在阿富汗却一直繁荣到7世纪,即后犍陀罗艺术(Post Gandhāra Art)。这时期石膏和陶制造像数量大增,可能是因为原料便宜又便于创作,无论是佛塔上的装饰还是尊像塑造均以石膏为主。5世纪初,笈多艺术渐进影响到西北印度地区,当地一些造像也出现薄衣贴体、螺发等笈多造像的特征。
笈多艺术给西北印度和北印度打上了共同的烙印,此后二者分别进入区域风格阶段,分别影响到中国西藏西部和西藏中部,导致西藏两种区域风格的形成。
从西北印度到阿里三围:
斯瓦特、克什米尔与中国西藏西部艺术的成型
6世纪以后,斯瓦特、克什米尔艺术逐渐发展起来。7世纪末至8世纪初,伊斯兰教把触角伸向中亚地区,然后入侵印度北部,西北印度逐渐伊斯兰化,佛教和印度教徒受到迫害,寺塔被毁。斯瓦特居于犍陀罗东北斯瓦特河谷中,克什米尔位于犍陀罗东部印度河支流的河谷中,均离开交通要道,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直到11世纪斯瓦特才告陷落,14世纪克什米尔终被征服,在此之前,佛教徒、艺术家纷纷到此避难,使得这些地区难得地保持了佛教文化的繁荣。
斯瓦特
斯瓦特古名“乌仗那”(Udyana),黄铜造像数量较多。斯瓦特铜造像的特点是颊颐丰满,双目大睁而无神,鼻梁扁平,身体健壮,肌肉匀称,喜用金、银、红铜装饰眼眸、嘴唇和白毫,具有强烈的本地化色彩。此外,斯瓦特造像均有笈多式螺发,虽然袈裟仍然有犍陀罗式的厚重,但“V”字衣领以及贴身的袈裟下肌肉凸现,以规则排列的线条表现衣褶,却是笈多艺术的特点(图4)。早期的斯瓦特造像多以莲瓣直接着地(图5),此后覆莲下加平台的情况更为常见,亦常见山石座和矩形鸟兽座。
斯瓦特对于藏传佛教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据说,被誉为藏传佛教“第二佛”的莲花生(Padmasabhava,8世纪)就是来自乌仗那国的王子。8世纪,应藏王赤松德赞(Khri-sRong lDe-bTsan,742—800)迎请入藏弘法,于779年创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克什米尔
古代克什米尔(Kámīr)位于斯瓦特东南,喜马拉雅山西麓的群山之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广义上,克什米尔还包括北部的一些地区,如吉尔吉特这个交通要道和佛教中心。这块相对封闭的弹丸之地,却是西北印度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长期以来受人景仰。佛教史上有名的第四次结集,即“迦湿弥罗结集”就是在此地举行的。
犍陀罗艺术衰微后,克什米尔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约在7世纪前后,一位名为杜尔罗跋伐尔檀那(Durlabhavardhana)的人建立了迦尔郭吒(Kārkoa)王朝。据说,玄奘到此地时,正值此王当政。迦尔郭吒王朝的国王多信仰婆罗门教,迦尔郭吒人将财富大量用于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建设。(图6)
克什米尔艺术虽然保存了一些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本地的风格特点非常明朗,如袈裟轻薄,肌肉强劲有力,胸肌饱满,晚期菩萨像披长长的花鬘,戴尖锐宝冠或花饰宝冠,身材拉长,腹部隆起四块肌肉。独特的坐具设计(如山石座、鸟兽座等),喜爱用红铜、银和彩石装饰坐垫、短裙和身体局部(眼睛、嘴唇、乳头等)。特别是吉尔吉特造像极好奢华装饰,造像精美华丽(图7)。另外,克什米尔造像作为密教中心之一,密教造像的数量更多。
克什米尔毗邻西藏西部拉达克地区,对于10世纪以来藏西佛教复兴以及佛教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过深远且长期的影响。(注5)
842年吐蕃末代赞普达磨(Dharma)被刺身亡,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Skyid lde nyi ma mgon)逃到西藏西部的阿里(mNga' ris)地区,通过与当地贵族联姻,于925年取得了古格—布让(sPu rangs,今普兰)的统治权,后又将古格(Gu ge)纳入治下,建立古格王国。尼玛衮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将领土瓜分,长子贝吉衮(dPal gyi mgon)占据芒域(Mar/ mang yul),后来发展成为拉达克(Ladakh)王国;次子扎西衮(bKra shis mgon)占据布让(sPu rang),控制了古格地区,成为古格王国;幼子德祖衮(lDe gtsug mgon)占据桑噶(Zangs dkar)三个王国,传统称为“阿里三围”(mNga' risskor gsum)。古格王国逐渐吞并另外两国,古格王耶歇沃(Ye shes 'od)重振佛教,古格王国成为佛教复兴的重要基地。(注6)
耶歇沃是扎西衮的儿子松艾(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去世)的法名,他放弃国王身份,出家为僧,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为此他派仁钦桑波(958—1055)等21名青年才俊去克什米尔学习密法,仁钦桑波成为后弘初期佛教振兴的僧人领袖,贡献巨大。耶歇沃于996年修建了著名的托林寺(mTho lding dgon),将之建设成佛教中心与译经中心。佛教复兴的运动带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仁钦桑波从克什米尔带来的工匠参与寺庙建设与尊神绘塑工作,克什米尔艺术的影响直接进入阿里地区。
耶歇沃之子强曲沃(Byang chub 'od)派人于1042年请阿底峡(Atīa,梵文名Dipakararījāna,982—1054)到托林寺住锡。阿底峡大师是孟加拉王族后裔,时在摩揭陀著名的寺庙超岩寺(也称超戒寺、超行寺,Vikramaīla Vihāra)任上座,到西藏西部以后,传法三年之久,著《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等著作,并与仁钦桑波一起翻译经典,促进了藏西佛教的发展。
随着穆斯林势力在西北印度的扩张,很多僧人、艺术家逃离当地寺庙时多携带神圣的法物来到藏西避难,他们携来的造像与本地的作品之间无论是艺术风格还是艺术水平都相当接近,要准确区分哪些是藏西本地作坊制作的铜造像,哪些是克什米尔的舶来品十分困难。(图8、9)11至12世纪藏西本地艺术家以模仿克什米尔风格的造像为主,偶尔独立创作的作品较为稚拙,水平不高。(注7)15世纪藏西进入黑暗期,铜造像数量少,风格不明朗。从保存的壁画来看,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西藏中部的影响进入这一地区,带来了波罗艺术风格。到了元代,尼泊尔艺术也传到此地。不过,虽然藏西艺术陆续受到其他地区风格的影响,克什米尔传统与本地艺术结合的风格仍占据主流,与西藏中部的造像形成鲜明的对照。
可以参考:11世纪西藏西部克什米尔风格黄铜泥金白文殊菩萨立像(拉萨大昭寺)
圣地落日:
东北印度、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中部艺术风格的奠基
东北印度
后笈多时期,戒日王(Haravardhana,612—647)统一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与繁荣。戒日王去世以后,8至12世纪,东北印度的比哈尔(Bihār)和孟加拉地区(Bengal,包括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孟加拉国Bangladesh)在波罗王朝(Pāla dynasty)和塞纳王朝(Sena dynasty)的统治之下,佛教进入最后的繁荣期,尤其是在摩揭陀地区达到顶峰,直到12世纪穆斯林军队横扫恒河流域为止。(图10)
波罗(帕拉)艺术首先兴起于比哈尔南部,即摩揭陀地区,这里分布着菩提迦耶(Bodh Gaya)、那烂陀(Nālandā)、库尔基哈尔(Kurkihār)等宗教与艺术中心。波罗造像主要以黑石造像与铜造像为主,黑石造像材质细腻,造像精致,装饰繁复,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图11)。
参看:10-11世纪印度那烂陀寺石雕释迦牟尼佛与二菩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那烂陀寺是东印度重要的佛教中心,兴起于笈多时期,唐代高僧玄奘曾到此学习,一直到10世纪那烂陀寺都是东印度佛教的标志,12世纪毁于穆斯林军队。那烂陀寺出土的铜造像共51件,其中23件属于波罗早期。
库尔基哈尔村距离迦耶(Gaya)东27千米,居于迦耶和王舍城(Rājagha)两大佛教重镇之间,是朝圣必经地,也是造像的艺术中心。从1847年以来,在遗址先后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佛教造像,其中大部分保存在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The Indian Museum,Kolkata)。库尔基哈尔村的铜造像大多数为黄铜,极少红铜鎏金,普遍采用错银和红铜装饰,很可能还镶嵌宝石和玻璃。(图12)
波罗造像用料厚重,身体宽厚,身体稍拉长,表情庄重,背光、莲座高大,程式化较重,有些还有非常精美的镶嵌。波罗风格的造像对后弘初期西藏中部造像有较大的影响。
尼泊尔
12世纪晚期,东北印度佛教之火焰被穆斯林军队扑灭,喜马拉雅山中的尼泊尔逐渐取代了东北印度的位置,成为影响西藏佛教艺术的重要来源。
尼泊尔北与中国西藏的日喀则地区相接,西北角与西藏阿里地区相邻。其他各方均与印度北方邦及比哈尔邦接壤。它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多受到东北印度的影响,又由于7世纪以来,唐—蕃—尼婆罗(今尼泊尔)交通线的开辟,尼泊尔的影响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西藏中部地区。14至15世纪,尼泊尔艺术一度成为西藏艺术的主流。
目前能见到的尼泊尔造像以离车毗时期(Lichavi Period,300—879)、过渡时期(Transitional Period,880—1200)和早期末罗时期(Early Mala period,1200—1482)为多。
离车毗艺术受萨尔纳特艺术的影响较深,铜像厚重,鎏金薄,造型质朴,身体板直,前倾。(图13)过渡时期佛教发展达到顶峰,尤其是金刚乘佛教流行,对于西藏产生重要的影响。印度教的性力(Shakti)信仰流行,对于晚期密宗的形成与传播影响很大,也是其造像内容不同于印度和中国西藏的原因。这时期造像数量增加,表明社会富裕,施主众多。这一时期铜造像多而精美,造像身材匀称,肌肤光滑,气质柔媚,制作精工,鎏金明亮。(图14、15)早期末罗时期,加德满都的艺术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末罗人来自尼泊尔东南部地区,受穆斯林军队的打击,逃往加德满都,与当地联姻。王朝晚期佛教渐趋衰落,印度教成为主流。这时期的造像装饰华丽,尤其是在宝冠、耳环、璎珞、腰带等部分纹样复杂,镶嵌众多,且喜用红、蓝宝石、玻璃、珍珠和各色次宝石镶嵌,用银丝作错嵌装饰。(图16)这些装饰手法对西藏山南地区丹萨替寺的造像产生了影响。(图17)
该造像可参考:14世纪尼泊尔红铜鎏金文殊菩萨举剑坐像(私藏)
如果说东北印度的造像对于中国西藏中部的影响主要限于后弘初期(10—13世纪),尼泊尔造像对于西藏中部的影响则是长期的,在14至15世纪达到顶峰,成为西藏中部艺术风格的潮流,直到15世纪中期以后,西藏艺术才逐渐展示出明确的本土风格。
西藏中部风格的确立
10世纪晚期开始,来自中国西藏中部的信众涌向东北印度这块佛教圣地,寻访名僧、名寺,修习密法,翻译经典,订制法物,他们携归的造像对于西藏影响很大。此外,12世纪以来,东北印度的佛教信仰屡受穆斯林军队打击,大量僧人逃入加德满都河谷避难,大量神圣法物也因此流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为西藏艺术家学习、模仿波罗艺术提供了素材。受其影响,西藏中部形成了受波罗艺术影响的风格,其造像的特点是以黄铜为主,背光高大,莲座宽厚,莲瓣肥大,身材壮硕,表情庄严,如聂塘卓玛拉康(sNye thang sGrol ma lha khang)的造像(图18)。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河谷一直是中国西藏与东北印度沟通的中转站,所以一开始,尼泊尔艺术家很可能是东北印度的模仿者以及尼泊尔艺术的创作者。受其影响,西藏艺术存在另一个流派,就是尼泊尔艺术影响下的西藏风格。在尼泊尔艺术的熏陶下,西藏艺术家学习红铜鎏金造像技术,工艺水平足以与纽瓦尔工匠比肩,如夏鲁寺(Zhwa lu dgon)的造像以及丹萨替寺铜塔上的造像等。(图19)藏族艺术家也创造出大量具有西藏特色的祖师像(图20),祖师像具有明显的西藏本土风格和人物特征,具有写实性,反映出祖师的内在精神,算是西藏最早的独立艺术创作。(注8)
结语
在常见的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图上,中国西藏地区总是空白,似乎西藏作为高原禁区,被世界所遗忘。这明显是错误的,无论是史实还是文物实例都可证明,西藏西部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活跃度,西藏西部的艺术就是在西北印度的艺术养分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西藏中部与尼泊尔、东北印度的通道是朝圣之路、学法之路以及艺术之路,大量的贝叶经、佛像、唐卡作为圣物从佛陀的故土被带到雪域高原的寺庙中,作为最珍贵的法物受到供奉膜拜,保存至今。从这一点来看,喜马拉雅山间的缺口和通道就像无数的血管,给青藏高原输送了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养分,才使这片贫瘠的土地开出了令人惊艳的佛教艺术之花。
从藏传佛教艺术史的角度来看,7世纪时,当青藏高原被周围的佛教世界包围时,这里还只是一片佛法的处女地;然而12至14世纪,当佛教信仰在青藏高原扎下了根,成为藏族精神世界的象征时,从西北印度到东北印度,从南亚次大陆到喜马拉雅山,周围的佛国明灯一个个熄灭了,雪域高原成为佛教的圣地和中心。佛教艺术在这里成熟、发展,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藏传佛教艺术。
佛陀之光
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
10.23—12.23
故宫博物院斋宫
文·图|罗文华,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注释
1. 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页。
2. Susan L. Huntington with constributions by John C.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 Weather Hill, 2001, p.116.
3. Ulrich von Schroeder, Indo-Tibetan Bronzes,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2008, pp.65-98;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I),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2001, pp.53-210.
4. R. C. Sharma, Buddhist Art of Mathura,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1984, pp.4-7, 27-28; Indian Museum ed., Mathura Sculputures: A Catalogue of Sculputres of Mathura School in the Indian Museum, Kolkata: Indian Museum, 2006, pp.2-3.
5. 罗文华,《故宫藏克什米尔风格铜造像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5期,第63—74页。
6. Ulric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2001, vol.1, p.69.
7. 霍巍,《西藏西部佛教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6—140页,图188—220。
8. 杨鸿蛟、魏文,《师道——辽楼居藏14至17世纪藏传佛教上师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国版2018年12月刊。原标题:《从南亚次大陆到喜马拉雅,藏传佛教艺术之源: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