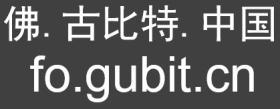侧边栏
藏传佛教造像的流派与样式(中)
直接承受了克什米尔影响.
1042年东印度阿底峡大师等先后被迎到古格弘法, 驻古格托林寺, 传法三年。其弟子仲敦巴创噶当派, 建热振寺(1056年) 。因此之故, 藏西的佛像也一定程度受到东印度系的影响, 据说益西沃请人制作的佛像, 质量非常优异, 与印度铸佛像非常相似, 极易与印度佛像混淆。
藏西的佛教艺术还包括拉达克王国,其原为古格王国支裔芒域一支, 位于今克什米尔东北部(拉达克王国首府称为“列”,是重要的克什米尔与西藏的边贸口)。
17世纪20年代, 由于古格国王信奉基督教而招致黄教集团不满,1630年黄教集团联合拉达克军队占领了古格, 古格王国灭亡, 1682年五世达赖派军队驱逐了拉达 克军队。
早期藏西造像多见为9至12世纪作品, 普遍造型有稚拙之感, 比例、动态上似乎不太协调, 但并不感觉拙劣, 而是有一种儿童画的感觉, 很纯朴可爱, 天真富有童趣。这是因为佛教初兴不久, 本地匠师尚处于模仿克什米尔等外来造像的阶段。例如图4的菩萨立像, 束冠的绪带沉重地上扬, 双腿如棒, 膝部呈球形, 是较为典型的藏西初期后弘期的作品。
此时的造像多以黄铜制作, 眼喜嵌银,大杏眼圆睁, 菩萨、明王装身具粗大, 持物如宝剑、金刚柞等亦显苯拙, 明王姿态夸张, 有如玩偶, 台座也多沿袭克什米尔,方座, 两侧饰狮子, 莲瓣简略宽肥(图5)。
菩萨束发高耸, 成梯形, 宝冠以三片饰片组成, 很简略。束冠的绪带在双耳上方结成扇形或团花结, 外形突出, 裙上饰有双行阴刻线, 上敲梅花点, 这也是克什米尔造像爱用的形式, 例如图6的莲花手观音, 但那柔软的动态, 肩两侧的莲花以及多层的莲花座又明显地来自东印度, 可以说是一件混合有克什米尔和东印度因素的藏西作品。
背光也常见瘦长的椭圆形, 边缘饰火焰或卷草, 喜镂空。
总之, 在西藏后弘期初期, 整体上样式多处于模仿、消化、发展的阶段上, 克什米尔和东印度的色彩浓厚, 有各别作品甚至在产地归属上产生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可不必过分拘泥于产地之争, 而重点是分析其属于哪种造像风格、流派,或者说是主流属于哪种造像系统。实际上藏西地区不止模仿克什米尔等外来佛像, 偶尔还可见模仿汉式佛像, 例如图7十一面观音立像, 据认为是藏西的作品, 整体样式及动态、台座、理路等细部明显系仿自唐代流行的小观音铜像。但那笑脸、大杏眼还有模糊不清的十一变化面以及莹润的黄铜质则又有克什米尔的因素在内, 应该承认其很可能制做于西藏西部。图8四面观音立像, 就是13世纪较为典型的作品。
13至15世纪的藏西造像风格最为鲜明, 造型一扫早期稚拙之风, 其比例匀称,身躯舒展, 手脚等极富写实功力, 宝冠、蹭带、耳环等制作得玲珑剔透, 细部凿刻花纹精美, 再加上被帛和卷草纹背光, 极尽浮饰之美, 其华丽流动的卷草背光可视为东印度帕拉风格在藏西的复兴。总之, 此期的造像呈现出夸张的, 外扬的跳动感,早期的垂于耳际的绪带变成曲卷外扬的取动样式, 被帛也往往制成圆环形, 由于细部过于雕饰, 轻盈剔透, 像背后要辅以梁架纠结各镂空部分, 以起加固作用, 有的背后饰物几乎纠结成网状(图)。整体造型呈三角形, 特别是台座呈大梯形, 底边外张,莲瓣宽肥, 尖端上卷, 台座边缘饰连珠纹。这种大梯形的台座是藏西佛像显著的特征之一, 极易辨识。
睑型多为宽额, 脸部略瘦, 五官刻划深刻, 肩毛突起, 眉弓部刻阴线。
藏西造像几乎均为黄铜, 繁金者较少, 制作精美者在眼白、缨路或台座敷布等细部嵌白银、红铜、或嵌松石, 色彩富有变化, 很耐看。
大体上说, 13至14世纪的作品浑厚优美, 虽强调装饰性, 但恰到好处; 15巧至16世纪后的作品, 则过分娇饰, 重在外表的玲珑华美, 此后不久, 藏西的造像艺术即衰落了。
藏西造像上一个值得注意现象的是由于密宗金刚乘发达, 以大日如来为首的金刚五佛, 在13至15世纪数量上颇多, 这些佛像都是以菩萨装出现, 他们在造型上没有太大区别, 只有凭借手印来确定佛名.
2、西藏中部的造像(14世纪前)
西藏前弘期的佛像所见甚稀, 据传拉萨大昭寺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像塑于唐代, 但后世装案过重, 是否为唐代原作也不可遮断。
1045年, 阿底峡在藏西传法三年, 即赴藏中, 成为以噶当派为首的佛教复兴导师。1054年圆寂后, 其大弟子仲敦巴创建了噶当派第一座寺院热振寺。到12世纪时, 佛教各僧团(包括前弘期的宁玛派)和寺院已遍布藏中各地。西藏佛寺与中印度特别是东北印度的帕拉王朝(约750年-1200年)的佛寺联系密切, 并以尼泊尔为主要经路往来, 故藏中造像上体现的尼泊尔和帕拉印度的色彩极为浓厚。此外在后藏的日喀则为中心的造像上于闻的因素也可发现。
在造像上一般将拉萨及偏南的日喀则及江孜这一大区域的风格统称为西藏中部样式。
10世纪至12世纪前后, 所谓后弘期的佛法恢复伊始, 由干阿底峡及其弟子首先是以西藏西部带动佛教复兴的, 因此, 早期中部的铜佛像风格与藏西风格接近, 有的不易区分产地。如略呈机械性的动作,愉悦的表情有如孩童一般, 且多以黄铜为材料, 眼部有的嵌银, 衣纹特别是腿部常见双阴刻线, 空白处凿梅花点的作法。
再稍晚一些时候佛像的台座及背光显然是模仿帕拉样式而来的, 一般带有四足,呈多层方台式, 也常可见带有横梁及靠背的金刚宝座式台座。立像多为瘦长的火焰形光背, 顶端有宝塔或金翅鸟, 背光为火焰镂空形。菩萨的饰物如飘带或手持的莲花及身旁的卷草飘逸婉转, 互相纠结, 这些细部特征也都是渊自帕拉晚期崇尚藻饰,追求华美的造像而来。
佛陀像的衣饰多是所谓萨尔那特式的, 大衣有如湿衣紧裹躯体, 除领口, 袖口及脚部简略刻划大衣的边际线外, 基本上没有衣纹, 佛立像的大衣俨然如披风一般拖于身后, 这种大衣样式虽渊自印度萨尔那特但却是东印度或主要还是尼泊尔佛像最爱用的手法。
总之, 13世纪前的, 特别是11、12世纪的西藏铜造像呈现着各种流派交汇的现象, 难于一言以蔽之, 因每尊像而异, 可分别体味出克什米尔的、尼泊尔的、东印度的主要倾向, 同时又杂揉有其他因素,也可以说, 西藏本土自身的较为定型的成熟的佛像样式正在孕育之中还没有形成。
例如图10的金刚萨睡像那白由扭曲的动态, 五官深刻的脸部, 肩两侧的莲花, 和那多层高台座及缘饰的连珠纹, 无一不是来自东印度, 与图2的东印度莲花手观音造型颇多近似之处, 但制作较为粗犷有力,莲瓣等较简略, 睑型宽阔, 五官甚至有克什米尔的手法影响。其铜质为黄铜, 因此推断其以东印度佛像为模本在西藏地区制作的较为合适。
3、西藏中部的造像(14世纪后)
14世纪中期, 即相当明代初期, 蒙元势力虽退居草原,但对明朝仍然是个威胁,明政府极为重视与西藏的友好关系, 也意在阻隔蒙古与西藏的联盟。而元朝一度在蒙古上层流行的藏传佛教, 在其退居草原后竟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直至200多年后的明末才又重新复兴。
14世纪中期, 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西藏美术上汉文化的影响有着突出的显现。此时的西藏中部造像样式可以说已经成熟并开始定型。此前的帕拉样式特点和克什米尔样式特点等多隐含不彰, 除西部地区自身特点尚强外, 西藏中部造样在样式上最易于指摘的, 仅可见尼泊尔样式的某些要素, 但这些要素与汉文化因素及西藏固有审美趣味相结合, 甚为融洽, 没有生搬硬套之痕迹。尼泊尔造像的过分强调宽额、阔胸、厚肩等都大为削弱, 细腻华丽的背光上的卷草纹及台座繁复的莲瓣纹, 以及强调衣帛的柔软质感等手法, 都无疑是吸收汉族艺术的体现。
西藏造像在吸收了诸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优美典雅的造像艺术。这一时期的造像比例极为协调,造型准确,细部刻划生动, 五官端正优美。或者说, 它将各式佛像造型上的偏激之处全部加以软化、弱化, 代之以一种新的、成熟的、恰到好处的造型美(图11)。
明永乐初年, 明廷开始大规模地铸造佛像, 作为与青藏宗教上层互相馈赠的礼品。宣德的带官款佛像也常现。永宣的造像样式优美, 是钦定的官式造像, 它虽然制作于内地, 但从制作风格判定, 仍以藏族或尼泊尔人为主, 骨干上尼泊尔风格尚存, 只不过在大衣、裙部等处喜欢细致地刻划衣褶, 以符合汉民族的审美趣味。
从明代史料记载看, 至迟在永乐六年(1408年), 佛像已成为双方通纳与祈福、吉祥的象征物。每年, 大批的青藏僧界人士以各种名义到明廷朝奉,礼品中必有佛像,明廷回赐超过进献物多倍的茶叶、丝帛等赠品, 内中也必有官造佛像。以致许多藏区僧侣想出各种名目赴京以希获回赐。在这种形势下, 起到了推动汉式的佛像与藏区的佛像在样式上趋于一致的倾向。故明代钦定的佛像和藏区的非钦定佛像也有许多造型上的共通特征, 有的造像虽然没有永乐、宣德年款, 但精美程度不下官造, 一般多推断为藏区所造(图12)。
藏区造像不同于汉地的喜用汉式衣着, 仍多采用无衣纹式的衣着, 可看作是远承印度萨尔那特式造像的传统并以尼泊尔造像为基本框架而来。在有的14、15世纪的造像上, 也能看到衣纹喜用双箍状,如双绳纹缠在身上, 这实际上又要追溯到马土腊造像的渊源。制作华丽的造像喜在无关紧要之处嵌松石、宝石, 致有画蛇添足之感(图13).
15世纪初, 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兴盛, 在拉萨及偏西南的日喀则以及江孜先后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仑布寺、白居寺等格鲁派寺院。在铜造像上, 以宗喀巴为首的高僧像较前为多。此时期写实水准空前提高, 故高僧的写实性肖像流行。14世纪之前的高僧像由于写实性技法所限, 故许多高僧像想来只是象征性的表现, 或者说从技法上看不出是否是真的肖似, 而17世纪以后的高僧像由于写实技法的衰退, 高僧像只注重造宗喀巴等少数祖师像,其它高僧像制作相对减少,且更流于形式化概念化, 只能凭僧帽、袍服、道具等象征性标帜来确认某位僧师。但只有相当于明时代的高僧肖像, 技法极为写实, 造型准确, 每位高僧像都各具相貌特征。我们虽然见不到本人, 但可推断 与本人肯定肖似, 有的虽仅十数公分高,但技艺是大手笔, 令人惊叹。反观清代有的高僧巨像, 大而空洞, 技法贫乏, 实不可等同视之(图14) 。
此外14世纪左右由梵文译成藏文的《造像量度经》在制作各类佛、菩萨、明王的样式上起到了重要的统一和规范化作用。1742年(乾隆七年)更由蒙古族的工布查布译为汉文, 此后的造像样式更趋统一, 而个性化减弱。
西藏地区的造像在14世纪后, 样式统一, 汉文化色彩加强, 另方面在17、 18世纪也即相当清朝康熙、乾隆时期仍制作了不少复古样式的作品, 其主要是以东印度佛像为楷模, 也有部分作品是刻意复古克什米尔样式。这些造像有的尺寸高大, 铸造极为精美。至今在北京故宫、承德外八庙等仍可见到。这些作品有些出自前藏,有的是专为进献清廷而特意铸造的, 其图样的选择是以东印度或克什米尔为准则。
这种佛像的出现, 似乎与乾隆帝的好古猎奇趣味暗有关联。此外也有不少小型像、可认为在大统一样式潮流下, 仍存在着各种刻意复古的流派。这些作品多铸造精美, 铜质精炼, 纹饰细腻, 手脚细部刻划极生动写实, 很可能出自西藏的尼泊尔人工匠之手。如图15的空行母, 即是仿东印度, 其手脚的表现引人注意。也有追摹克什米尔佛像之作的乾隆御制佛像, 其严整的造型及写实的手脚, 应系出自非汉族工匠之手。
西藏地区相当于元明时代所造的小型铜像和分段铸出像, 由于铜质较柔软, 器壁较薄, 多采用以包卷底部器壁的方法来固定底盖, 这个做法是明显区别干清代北京和蒙古一次性铸造的黄铜像的所谓斧剁底即周壁锉出毛刺来固定底盖的方法。但大型铸像, 特别是整体一次性铸出的20、30公分以上的铜像, 由于器壁较厚, 铜质坚硬, 明代的永宣铸像也以剁底法固定底盖。此种方法在鉴定小型铜铸像上可以参考, 特别是清代北京和内地铸像几乎无例外都用剁底法, 但也要灵活掌握, 因像而异。
大体上, 西藏12、 13世纪(相当于元代)的铜像铜质除红铜外还有黄铜、不夔金像较常见。而14至17世纪前后也即相当明朝时期造像则多红铜, 婆金色调偏暖,倾桔黄色, 18世纪前后的清代北京及蒙古铜像多黄铜铸造, 姿金呈柠檬黄色。另方面西藏铸像讲究多种铜料和配方, 故铜质色泽呈多种变化, 尚须灵活运用, 主要还应从造型分析其产地和时代。
4、藏东地区佛像
拉萨以东, 以昌都为中心的康区(旧西藏四部之一, 也称喀木)和安多地区(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一带的藏区)在西藏佛教美术上一般归人藏东流派。
藏东佛造像的面貌较难于邃断, 因其地域偏离拉萨接近汉族地区, 一般所见国外图录上, 似乎把凡与上述几大类造像风格都对不上号, 且含有较多汉文化因素的作品判断为藏东地区所作。所以, 藏东地区的作品实有待实地考察。
西藏东部以噶举派的支派噶玛噶举派最具影响力, 噶举派流派众多, 支派也多分布康区。噶玛噶举派以都松钦巴(西康人, 1110年一1193年)为第一世噶玛巴, 后世噶玛巴曾受元、明两代册封, 主寺多在前藏。
巧世纪初期, 噶玛巴与明朝皇帝关系密切, 以此带动了汉藏文化交流。在藏东形成了噶玛噶底画派, 其始于16世纪晚期, 至18世纪最为兴盛。此派所绘唐喀以青绿山水著称, 罗汉像、大成就者、祖师像占有相当数量, 画风有显著的汉族艺术影响。
东部地区的铜像早期作品所见较罕,一般多为14世纪以后作品, 首先从题材上看, 以米拉日巴、玛尔巴等为首的祖师像和罗汉像数量上明显较其他地方造像为多,这与噶举派支派众多有关, 而罗汉像显然是依据汉族地区的罗汉画图样而来的。
藏东的铜像在风格上朴素明快, 多注重远观大效果, 在细部刻划上不太重视过度的装饰与雕琢, 故显得简洁、单纯。造像上的外来影响, 即尼泊尔风格、克什米尔式风格等一般轻易不显露痕迹, 汉式风格显著。那些高僧像上所显现的只是老老实实地尽可能周到写实地表现衣着和头部及手部, 尤其是脸部的刻化, 极为写实, 如见其人(图16-18)。铜造像的铜质除鎏金像外, 黄铜不鎏金像也有。
5、藏传佛教流布区
在敦煌莫高窟, 斯坦因发现的9至11世纪的帛画也可以看到与铜造像风格一致的倾向, 如观音立像, 头戴三枚叶片式宝冠, 宽额, 肩部丰满, 双腿粗壮, 裙部的螺旋纹, 都可发现尼泊尔和克什米尔, 乃至斯瓦特的因素, 双眼特意以白粉敷色,与克什米尔铜像眼部嵌银的意趣是相同的。又与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哈拉浩特(西夏黑水城,今额济那旗黑城子)发现的帛画, 应作于1227年成吉思汗攻灭黑城子之前。
在这些帛画上可看到, 佛陀头部硕大,呈倒置梯形, 额头极宽阔, 五官集中, 肩部饱满宽厚, 双膝敦厚结实。菩萨身躯呈S形, 富有动感, 高束发。以上这些都是西藏佛教艺术随吐蕃势力而流布西藏本土之外的实例。这些帛画的作者是藏族人,却属于用所谓尼泊尔语言所表现的帕拉风格, 也可以说这些出自藏族画家之手的风格里又包含着尼泊尔式的帕拉因素。
13世纪时, 西藏除藏西佛像尚保留较强独自风格外, 西藏广大地区乃至内地,佛像的印度、克什米尔等色彩逐渐减弱,以尼泊尔造像为骨干确立了西藏佛像的样式。这种现象的背景, 应是元朝独尊萨巡派的同时, 以后藏日喀则萨迎寺为大本营的萨逛派佛教美术发挥了重大影响。萨逝派尤以学术著称, 历代高僧译著颇多, 佛教美术也赖以广布内地。萨迎派与尼泊尔在历史地理方面关系密切, 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美术依然未脱出尼泊尔的影响, 如北京居庸关和杭州飞来峰。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中统元年, 1260年入中国)曾在北京及元上都(今内蒙古正兰旗南)制作了许多佛、释、道塑像, 可以知道, 在13世纪时, 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的流行。直到明代, 北方汉传佛寺的佛像及单尊铜像仍不 时看到西藏佛像的时隐时彰的影响。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金铜大黑天像, 从风格分析应为西藏中部所造, 恰与飞来峰金刚手石雕为同年所造(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 是极为珍贵的对比资料。又有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金刚手像, 也应为13世纪末西藏中部, 或者是后藏所造。甚至可以参考国外收藏的金刚手唐喀, 画风分析也疑为后藏。这数尊像尽管分布广泛,材质各异, 但整体造型及细部刻划都有着极为近似之处, 这种肥短身材、杏眼圆睁的明王造型是西藏中部甚至是后藏13、 14世纪的定型样式, 从中不难看出尼泊尔西藏风格如此广泛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图19-20).